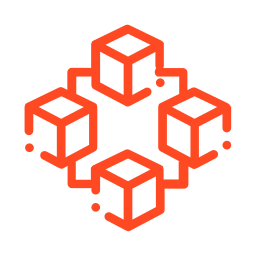87岁老人笔耕半生,只为还原史上最“刚”宰相王安石
长沙晚报掌上长沙12月5日讯(全媒体记者 肖舞)日前,一部由87岁长沙爹爹创作的长篇历史小说《铁腕拗相王安石》问世,持续引人关注。这位耄耋老人叫罗少亚,是一位退休电影工作者,耗时四十余年,十易其稿,将半生心血凝铸于此书。这不仅是一次文学创作,更是一场跨越千年的精神对话。记者今日专访罗少亚先生,聆听他与王安石的故事,以及这场漫长跋涉的思考。
记者:您对王安石的研究始于1970年代,最初是什么打动了您?
罗少亚:当我读到王安石的文字与事迹,被一种“天变不足畏”的魄力和“九死其犹未悔”的执着深深震撼。他不只是文学家,更是一位将崇高理想付诸实践的梦想家与行动者。那种在重重阻力中奋力向前的身影,让我这个中文系学生看到了文学之外更厚重的东西——一种担当的精神。那是一次跨越时空的“心灵认领”。
记者:从萌发念头到成书,四十余年、十易其稿,您如何坚持?最大困难是什么?
罗少亚:与其说“坚持”,不如说“欲罢不能”。王安石成了我精神世界的一个重要坐标。写作因本职工作而时断时续,但种子始终在生长。最大困难有两个:一是“辨伪”。传统史书对变法多有曲解,我需从大量笔记、年谱中剥开迷雾,寻找真实的王安石。二是“时间”。在职期间写作碎片化,事倍功半。直到退休,才能系统梳理。这就像老牛力耕,不觉已用大半生。

记者:您选择用历史小说而非学术传记来立传,如何平衡历史真实与文学虚构?
罗少亚:我尊奉“大事不虚,小事不拘”。所有重大事件、人物立场、变法核心,必忠于史料。但历史记载多是骨架,小说需血肉与呼吸。比如,史载王安石思考时爱嚼石莲,我便写他嚼到口腔流血;记其生活简朴,我便设计他吃饭只夹眼前一盘菜。这些是基于史实的合理延伸,目的是让人物立起来,有温度。
记者:书中对苏轼、司马光等“政敌”的描写很深刻,尤其展现了王安石“只有政敌,没有私仇”的胸怀。您如何看待这种境界?
罗少亚:这是王安石人格中最令我敬仰的一点,也是古代政治中罕见的君子之风。他与苏轼、司马光是“君子之争”。苏轼下狱,王安石虽政见不同,却立即上书疾呼“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?”这是何等胸怀!苏轼后来目睹新法某些益处,晚年拜访王安石时慨叹“从公已觉十年迟”,这是基于真诚的和解。
至于司马光,他们是旧友,因理念决裂。书中写王安石晚年听闻新法尽废,彻夜难眠,用手指反复划写“司马光”三字,内心充满痛苦,却无人身攻击。这种将政见与私德分开,保持对对手人格的尊重,在今天看来,依然是极高的政治修养。
记者:您的电影工作背景,对小说创作有何具体影响?
罗少亚:电影的核心是视觉化和动作性,依靠画面与台词推进叙事。这使我写作时,会不自觉在脑中“拍摄”场景,注重对话的节奏与表现力,力求每段对话都能推进情节或揭示性格。我也构思了一些功能性人物,如道士、义士等,他们像戏曲中的角色,既能串联情节,又能以其诙谐视角评论世事,增加可读性与节奏感。这种对“画面叙事”和“台词张力”的追求,或许是我的写作特点。
记者:您认为王安石及其变法,留给当下最重要的精神遗产是什么?
罗少亚:我认为至少有三层:第一是“立善法于天下”的法治追求。良法是善治的前提。第二是“为民尽心”的赤诚初心。一切改革若脱离人民福祉,便是无源之水。第三,也是我最为触动的,是改革者“认清真相依然热爱”的坚韧担当与“无私敌”的清澈人格。改革之路从来布满荆棘,需要理想主义者拥有强大的内心和纯粹的目的。王安石身上那种将国运扛于己肩的自觉,以及在巨大阻力前展现的近乎固执的韧性,对于任何时代的开拓者,都是一种精神的烛照。我写这本书,就是希望这烛火,能穿越时空,给更多人以光亮。
>>我要举报